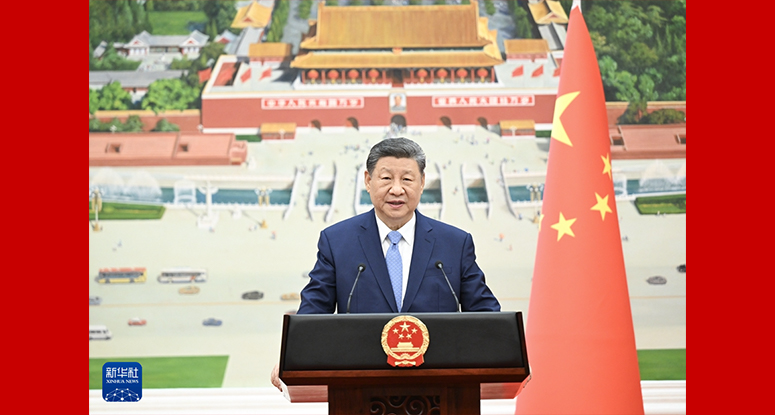新疆吐鲁番哈拉和卓墓地:再现汉唐文化融合下的生活图景
春节前,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发布《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地·哈拉和卓卷》,正式公布对哈拉和卓墓地考古发掘的研究成果,为这项延续多年的考古发掘画上了句号。其中的惊喜与谜团,让人更加关注这所尚鲜为人知的墓地。
一批古纸:中国纸和造纸技术向西传播的印证
临近夏天,人们习惯戴个墨镜来遮阳。可有谁想到,这个遮阳的眼镜早在唐代就有人戴了,虽说不是镜片做成的,但它的功效却是一样的。这件珍贵的历史文物就在新疆吐鲁番博物馆,它是一件唐代的铜眼罩。
这件形似双眼,用铜片敲击而成的眼罩,经鉴定年代是唐代高昌王国时期。它双眼部位两端尖,中间圆弧,中有条状铜片连接。面部凸起,背呈凹状。两个眼珠部位有三排各10个小透孔,上下排各3孔,中间4孔,眼罩左右边沿各分布有四五个透孔。眼罩面和背的边缘均有缝缀或残留的丝织物残片,这表明眼罩边缘缝缀的丝织物是为了佩戴时令其不直接接触皮肤而设计的。
更有多件纸质文物,从研究者的研究报告中可知,这些纸张的年代在晋代到唐代,是新疆出土时代较早的一批古纸。通过对出土古纸的纤维和制作工艺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从晋代到唐初,吐鲁番地区的纸张原料主要是苎麻和大麻,也出现了构皮造纸,多数纸张的原料来源可能是破布。在抄造纸技术上,有浇纸法造纸、抄纸法造纸,说明当时处于两种造纸方法并存的时期。在纸张的加工方法上,出现了单面和双面的表面施胶、浆内施胶加填等工艺,并有表面染色技艺,说明加工纸张技术已普遍应用于各种用途的纸张,成为中国纸和造纸技术向西传播的高潮时期。
出现内容如此丰富的文物的地方,是新疆吐鲁番市哈拉和卓墓地。
说起哈拉和卓墓地可能许多来过吐鲁番的人都不知道它在哪里,但许多来过吐鲁番的人都知道阿斯塔那墓地。哈拉和卓墓地与阿斯塔那墓地一路之隔,它位于吐鲁番市东约42千米,距著名的高昌故城南约5千米。
据说,哈拉和卓是古代一位大将的名字,他死后,人们称其生前驻地为“哈拉和卓”。现名为“二堡”。高昌故城北原来是一片茫茫戈壁,居民死后大都埋葬在这里。公元13世纪末高昌城废弃后,城北新建的哈拉和卓居民村把墓地分成为东西两部分,就有了阿斯塔那古墓群和哈拉和卓古墓群之称。
汉元帝初元元年,即公元前48年,中原王朝在此设置了“戊己校尉”。前凉建兴十五年,即公元327年,张骏在此设置高昌郡。这里文物众多,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吸引众多外国探险家大肆盗掘,攫取了大量珍贵文物。中国考古学家黄文弼1928年和1930年两次到吐鲁番进行考察与发掘。新中国成立后,新疆加大了对吐鲁番地区文物保护与发掘力度,先后对哈拉和卓古墓地进行了多次发掘,出土了众多珍贵的文物。前面说的铜眼罩,就是其中一件。
彩绘木鸭:“事死如事生”的丧葬文化融合
考古工作者从哈拉和卓墓地发掘了69座古墓,发现多座古墓里均有陪葬的木鸭。吐鲁番地区地处欧亚大陆腹地,属于典型的大陆型暖温带荒漠气候,日照充足,热量丰富,降水稀少,极度干燥,无论历史上还是现在,都不适合养鸭子。可古墓里却出土了众多的彩绘木鸭,这是怎么回事呢?
专家们对这些彩绘木鸭与1978年湖北省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彩绘鸳鸯盒”等相似文物进行认真比较研究后认为,它不可能是真的鸭子,而是鸭形酒具。再看吐鲁番地区自南北朝时期已盛产酒类,当地居民有饮酒的习俗,从而得出“无论从外形、形制,还是从构思来看,都有可能是酒具”的结论。
追根溯源,彩绘木鸭陪葬,反映的是一种民族之间文化融合现象。彩绘木鸭的“原形”来自内地战国时期至唐代墓葬随葬品中的鸭俑。哈拉和卓古墓里的彩绘木鸭虽然有中国古代“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成分,但它并非像汉代墓葬随葬的家畜家禽类动物俑可视为是对当时社会一般家庭生活真实的反映,而更大程度上显示的是逝者对曾经有过的美好生活的留念和追忆。
哈拉和卓古墓里还发现众多的壁画。虽说有些壁画画法简单粗糙,但表现出来的内容却令人印象深刻。
标注为M96号的古墓北壁上,有一幅宽1.68米,高0.45米的壁画:上半部用墨线绘出的长方框代表田地,下半部绘弯曲的枝条,似为葡萄园;男女墓主人并排席地而坐,男主人穿阔袖长袍,手执团扇。女子头梳双髻,手执一长棍(可能是一长拂);左上部为木俎,上置陶盆,盆内有一长柄勺,另置两器皿;下部绘一男仆,其前为三脚炉灶,上有一陶盆,盆内也有一长柄勺;右上角为一磨盘,画面破损,无法辨识。从这幅壁画内容看,应该是墓主人生前的生活场景。在标注为M97号的古墓北壁上,也发现一幅壁画。壁画绘在用白灰涂抹的砂砾石墙面上,画面四周用粗墨线条构框,其内划分为数格。在六个不同形状的方框内,分别画了六幅画。从画面人物的装束来看,既有汉族,也有当地民族,是一幅当时地主庄园生活的写实画。
哈拉和卓古墓内出土众多纸质文物,有各种各样的契约,有来往书信,更有一些墓志,这为研究当时的社会经济生活,提供了众多资料。另外出土的丝制品、锦制品,让我们看到了当时这里人们生活的富裕程度。众人熟悉的伏羲女娲图,在这里就出土多幅。而一些代人木牌的出土,让人们了解到当时的一些习俗。一些代人木牌一面有汉文红色的“代人”两字,另一面则是粟特文字,从中可知,当时这里埋葬的人群来自不同的民族。
棉制怪兽:诸多出土文物的谜团仍待破解
在人们熟悉的一些出土文物中,一些奇形怪状文物的出现,至今仍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一件哑铃状器物,虽已断为两截,但仍可看出它的原样。它两端粗,中部细,器物上有一道道削痕。
出土的握木,均呈亚腰状。中间稍细,两端略大,端尖平齐,表面留有一道道削痕。其中一件中部表面残留有包缠的丝织品。两层包缠丝织物,里层为数层白绢织物,外层为数层彩色织锦。
标注为M60号的古墓内出土了一件用棉面制作的怪兽。它用棉面制面,内絮棉花。此怪兽的头部有3条并行弯曲的鸭喙样物,三喙之间分别缝缀一个扁平半圆形小布囊,内絮棉花。中部一面缝成2个似为乳房的突状物,下部缝成2个大体对称的半圆形,似表示臀部。在半圆形的中间及其下部两侧,又缝缀3个半圆形小布囊,内絮棉花。怪兽的表面有用针随意缝缀之处。这个怪兽长30厘米,宽38厘米,高29.2厘米。它是做什么的?至今无人知晓。
这些出土文物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呢?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但不可否认的是,从哈拉和卓古墓现有的发掘中可以看出,这里与中原的关系十分密切。这种联系不仅在生活物资的联系上,更在文化融合上。特别是文化的融合,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融入当时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本报记者 王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