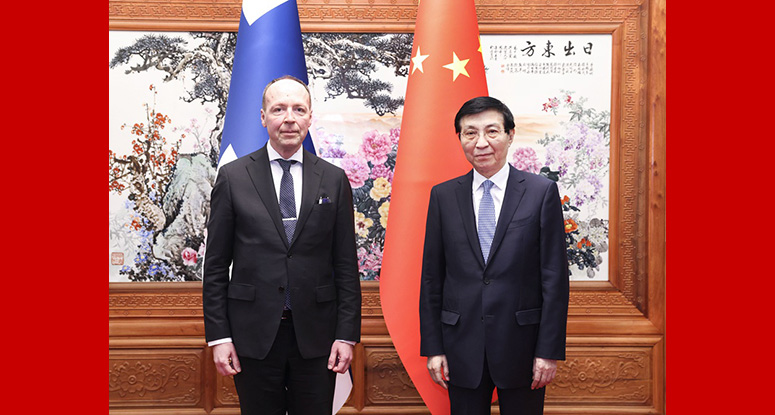那些年 中国人曾舍命护书
那些年 中国人曾舍命护书
终于等到“4·23世界读书日”,似乎适合来讲《炮火下的国宝》的故事。
这部去年11月在央视首播的六集纪录片,我一直心念至今。
上世纪30年代,日军侵华。早在1894年秋甲午战争期间,就由日本宫中顾问官兼帝国博物馆总长九鬼隆一起草制定的《战时清国宝物搜集方法》,又像压城的阴云密布中国的上空。危亡之际,上至政府官员、文人学者,下至图书馆员、普通工友乃至军人士兵,一场无数志士仁人义不容辞、抛家舍业、守望经典的古籍文献保卫战,在中国各地秘密而艰难地打响——
北平图书馆善本秘密南迁,并将部分善本运至美国寄存;清华大学珍贵图书辗转西迁重庆和昆明;郑振铎等人组织“保存会”在上海孤岛竭力抢救江南文献;浙黔两省战时联手共护文澜阁《四库全书》;八路军虎口夺取《赵城金藏》并妥善保护;齐鲁稀世文献密藏四川乐山……
一个个艰辛备尝、跌宕传奇,事关义气、职责、坚忍和希望的故事,2020年11月13日在北京“杜兴工作室”,我听《炮火下的国宝》总导演杜兴,向我一一道来。
事隔十年我一听
这不就是我当年关注那批书吗
北青报:跟这段历史的渊源是怎样的?
杜兴:2008、2009年的时候,我在《看历史》杂志当编辑。有一天翻《传记文学》读到一个回忆,说抗战期间国立北平图书馆曾有100多箱书,包括最珍贵的敦煌遗书、宋版书、《永乐大典》等,被辗转送到美国寄存。我就很惊讶,这么大事我从没听说过。
因为《看历史》创刊,前几期都是跟抗战相关的。比如我们最早一期就叫《日军侵华耽误中国多少事》。一直很关注抗战,但都没想过还有这个角度。我就编了一篇稿子,非常仓促,基本上口述作为基础,然后又查了一些其他论文,标题忘了谁定的,就叫《炮火下的国宝》。
北青报:十多年前的事。这么长情一个选题。
杜兴:到2017年,我已经做纪录片了。有一次纪录频道一个选题策划会,请了几个专家。其中一个专家叫张志清,是国家图书馆副馆长,也是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副主任,他对于这个选题非常非常重要。
那个策划会的主题,其实是讲传统文化、经典文化传播。张志清就讲,经典文化其实有一个载体就是书,书的故事其实很好。他说他曾经在图书馆界,让各个图书馆都做了自己过去怎么保护、抢救古籍的有关史料发掘,慢慢有一个主题就凸显出来——抗战时候那些古籍都很不容易。然后举了几个例子。我一听,这不就是我当年关注那批书吗?
他当时讲的几个例子我听了非常感动。尤其感觉厉害的是,当年不光政府,或者说那些图书馆的人或者大学者有这个意识,过程中有很多普通人,真的叫“侠肝义胆”。比如说《四库全书》当时从浙江往贵州搬的过程中,中途还曾落水,很多人去帮忙把它捞起来、又晒干。还讲到山东图书馆有一个人,1937年从山东走,1950年才回去,5箱书一本不少,他就是一个普通工友。
我一边在下面听,一边就给纪录频道的领导发微信,说这个我关注很久了,之前我们也写过这样的稿子。领导说好啊。接下来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我就跑到国图去找张馆长。他是一个非常有激情的人,也很会讲故事,脑子里细节非常多。聊了一上午,我录音回来扒材料扒出几万字。
我就觉得我们讲经典文化、传统文化,那些思想内涵当然很重要,但它载体的命运也很重要。那些古籍之所以贵重,不仅仅因为它是文物、它是宋版书、它上面记载的是孔子或者苏东坡的思想,也在于后面他们是怎么把它保护下来的,这一切是怎么沉积下来的——它的价值不是说书印出来那一瞬间就成型了,它是一个不断累积的过程。
北青报:这个开始很动人。之前还以为你们是受了比如说国图的委托,才来做这么一件事。
杜兴:不是。这个片子就是央视出品,国图是协助拍摄,全国有很多图书馆都大力协作的。
国家多难,政府内迁之际
谁还会留意到文献的保全呢
北青报:那接下来?那是2017年?
杜兴:对,很早,三年多了。接下来第一步先做案头。
得益于国家图书馆和全国很多省市图书馆之前做的抢救性的工作,有档案,包括当事人口述的整理,有些也写过文章,编过文集。图书馆这个还是很厉害的,这是很重要的基础。
一上来就发现好多故事都非常好,但是我们只有6集,只能选了又选。目前选的6集都是有一定代表性的。比如第一集《平馆善本避难记》,当时国立北平图书馆的故事,确实是全国的精华,不用说了。
第二集《焚余的清华瑰宝》,清华作为大学图书馆的代表。其实调研过程中发现,不光是清华,像武汉大学、中山大学,他们抗战期间跟书相关的这种转运史、抢救史,故事都非常的丰富。
北青报:第三集《孤岛大抢救》,上海、香港的故事。
杜兴:当时郑振铎和张元济他们,在上海组织了一个“文献同志保存会”。“中国的书在江南”,江南一带有很多藏书楼,比如嘉业堂。抗战期间大量的藏书楼遭逢变故,有些人死了或因家道中落,很多好书都流散到上海。郑振铎非常爱书也懂书,他发现这样下去,很多书就要被欧美人或者日本人买走了。
北青报:“私念大劫之后,文献凌替,我辈苟不留意访求,将必有越俎代谋者。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奇耻大辱,百世莫涤。”郑振铎《劫中得书记》里的话。
杜兴:他就写文章呼吁大家一定要把中国的书留在中国。刚开始他就自己买,后来发现力不能支。因为毕竟还要花钱的,而且很多古籍很贵。他就给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写信,说我们不能这样,我们得有组织地做,然后得有钱。
北青报:“在这个国家多难,政府内迁之际,谁还会留意到文献的保全呢?然而教育部立刻有了回电,说教育部决定要购置。这电文使我从失望里苏生。”这出自他的《求书日录》。
杜兴:后来就从中英庚子赔款退回的款项中拨给他们一部分,他们就抢购了很多很多。这个故事还非常曲折。其中有一批书需要从香港转运美国,但是香港沦陷,原定搭载的轮船开出港口就被日军炸沉了。郑振铎听到消息痛不欲生。但两年后得知,由于他坚持那批书全部重新整理盖章,那批书没赶上那班船。后来被掳掠到日本帝国图书馆去了。
抗战胜利之后,中国有一个追索委员会,王世襄他们跑到日本去参与索赔。其间发现这批书好像是我们的,上面有国立中央图书馆的印章。因为郑振铎非常细致,所有他接触的书都有细致编目,而且每部书上都盖了“文献保存同志会”的印。最后一对,对上了。就把这个编目作为证据,把那批书从日本那边悉数讨回。
当年这批书回到上海码头之日,被郑振铎派去接船的人有一个今天还活着,谢辰生。那老爷子大家都知道,文保界的一面旗帜。我们这部片子的片名就是他题写的,《炮火中的国宝》。
专门找了条船去走三峡
为了要身临其境
北青报:第四集《〈四库全书〉的抗战苦旅》。
杜兴:浙江省立图书馆的镇馆之宝——140箱文澜阁《四库全书》,加上88箱善本,当时从杭州一步步西迁,最后藏在贵州一个山洞里边,一直到抗战胜利。历时8年又11个月,行程2000多公里。
北青报:从建德往衢州龙泉县那次转移,运费无从着落,馆长陈训慈“又回到老家,因为急用,他只好压低价钱去出售谷子。最后凑了200块,这样刚刚凑满运费”。“非常令人感慨的是在离开官桥老家之前,他跟他的夫人说,你们自己逃难去吧。他大女儿我在2014年问她的时候,她还泪流满面,觉得她爸爸真的是太伟大了,就一句话‘你们逃难去吧’。”这段浙江工商大学副教授吴忠良的回忆让人听来实在是……
杜兴:第五集《虎口夺经》是八路军抢运《赵城金藏》的故事,这也是非常特殊的一段经历。
北青报:是,“金代汉文大藏经《赵城金藏》5000卷,和《永乐大典》、敦煌遗书、《四库全书》,被誉‘国图四大镇馆之宝’。因为现于乱世,它经历过更多的颠沛流离,最为惊险的一幕是抗战中八路军的秘密抢运。”
杜兴:第六集我们想在省图书馆里选一个。山东图书馆的故事实在太好太精彩。包括他们图书馆内部人都说,山东那一集,很多人看得流泪。
其实省图书馆有很多故事都非常精彩,像安徽图书馆、南京图书馆。还有湖北图书馆当时搬到鄂西,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还开架阅览,为当地研究、学习提供帮助。
北青报:做案头,选故事,然后呢?
杜兴:第二步就是广泛接触,实地调研。实地非常重要,你会挖掘到更多的细节。
北青报:听说你们还专门找了条船去走三峡,说要身临其境。
杜兴:对,看上去这好像对片子没有那么直接的帮助,但是很重要。包括跟那些老人聊天、跟他们后人聊天。因为后人跟那些老人接触过,你会感觉不一样。
比如说清华大学那个唐贯方,1938年1月他和同事护送977件书籍、仪器到宜昌。当时军政人员、军队、工厂、学校大量转移,船只不够,都囤积在宜昌。只有卢作孚的民生航运公司少量船只,吨位又小,一票难求。他当时在宜昌等了两个月。
我去他儿子家,他儿子说爸爸跟他讲,当时大家都买不到船票,都堵在三峡。头顶上日本飞机一直轰炸,那些书籍、仪器都堆在码头,露天的,临时搭一点什么棚遮挡一下。他还要每天大半夜起来,拿手电筒到处照一照,看哪里是不是丢了,是不是散箱了,下雨会不会有苫布没有盖好。身上随时还带个榔头或者什么,整天在那儿转着守护。
有些东西很重要
你都得在拍摄前感受到它们才行
杜兴:包括刚才讲山东图书馆有一个工友叫李义贵,他1937年走的,走之前儿子和老婆都不知道他干吗去,儿子才不到一岁。1950年重回济南,他老婆已经改嫁了,因为后来失去音信。你想一出去就十三四年,他儿子都已经成人了,说怎么突然冒出一个爸爸,他无法理解的。
这个儿子后来在北京工作,我在紫竹院见到他,跟他聊天,非常感人。他说他爸爸不太会表达感情,所以他们父子关系并不好。后来爸爸想办法送他去当兵,那时候当兵是很好的前途。入伍之后爸爸给他写了封信,他看的时候才哭了,爸爸用书信表达对他的一些愧疚。
这些东西很重要,你都得在拍摄前感受到它们才行。
北青报:真的很难想象,那十几年他一个人护着一批书在异地。
杜兴:开始是三个人,后来另外两个人都因为各种原因离开了,就他一直待在那儿没动。起初,还能定期收到寄来的津贴。后来随着战乱加剧,通信愈发不便,汇款逐渐时有时无。
北青报:“迫于生计,我只能去江岸搬运,清淤除污,担砂扛石,给人帮工,摆地摊,卖香烟,售菜果,朝出暮归,自炊自食,以微薄的收入借以糊口。”片子里有他之前留下的口述。
杜兴:他的外孙女叫刘蕾,在山东省博物馆工作。我们带她一块儿去乐山大佛,看她外公待过的地方。那种感觉是很特别的。最后她在采访里讲,说她一直想他一个人在那儿怎么活。一个山东人跑到乐山去,语言也不通,吃也吃不惯,住也住不惯,估计那个住的地方连电灯都没有。
北青报:嗯,看到她在片子里说:“文物放在山洞里面,他就在山洞附近守书。我想点灯一定是不会有的,黑黑的,就到天亮的时候,才能见到阳光。在当时战乱的情况下,他要有多大的胆量,在那么混乱的时代下,自己生存。”
杜兴:当时采访就在山洞那儿做的,那种时空的穿梭感特别强。你看那边寺庙还在,大佛也还在,再想想七八十年前。你就发现虽然过去这么多年,但有些东西它是不变的,有时候你会找到一些比较恒定的东西在。
其实我们这个片子,在呈现方式上没有任何的创新。所有手段都是大家用过的——基础的史料、档案、口述。寻访感的纪实拍摄用了很多,因为我想用它把古今能够串起来。虽然只是拍到现在的,但是你能感觉到当时和现在,其实很多地方是没有变的。
北青报:你们用一些插画挺好的。
杜兴:对,比如就像第六集讲山东的一批书,藏在乐山大佛寺旁边的山洞里。他们刚刚从乐山城转到大佛寺不久,就发生了乐山大轰炸。当时王献唐(山东图书馆的馆长)就写日记,说站在乐山大佛旁边,看到36架敌机飞过,然后城里面就一片通红,他感到非常惨烈。这种的呈现,我们就找人画一些插画。
再危难、再世道不济的时候
该做的事你必须还得做
杜兴:实地还有一个好处,你会近距离接触到古籍,亲眼看一下宋版书到底什么样子、敦煌遗书什么样子,感觉是不一样的。其实大家经常忽略,书也是一个物,本质上它和一个商代的青铜鼎没什么区别。是个物,就意味着它会损毁,它毁了就毁了。亲眼看到那些物,可以建立一种意识,这也很重要。
北青报:做这个片子最难的是什么?
杜兴:涉及到背景交代的一些东西,我们没有什么大的拓展,基本上都是这些年大家能看到的一些资料。那我们怎么弥补呢?我们用了大量当事人日记,幸好还有日记。第二个还很重要的是档案。
我发现我们的档案很厉害,就你能看出在当时那样一个情况下,整个公文系统它是非常健全的。这你不得不佩服。
北青报:我觉得当年那些人真是不错。那样的乱世,还都守土有责。
杜兴:对。你会看到很多东西都有完整的记载,会发现各系统它整个运转其实一直在。比如虽然说在战乱,当时国民党还建了个国立中央图书馆。中央图书馆其实啥都没有,就一个牌子。但蒋复骢他们那个时候大家非常郑重,每天公文来电,他还亲自从重庆飞到香港,再潜伏到上海接头。非常有意思,这种公文系统、联系网络没断过。
北青报:而且他们那些工作也挺有延续性。
杜兴:对,就是这样的啊。当时就说这批书抢救了之后,以后只要光复,我们新的中央图书馆一定要用的。大家有这种必胜的信念,而且工作照旧。
所以这就回到我最想说的一个问题,就是做这个片子,除了国宝之外,我们到底关注啥?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责任心。不管世道再乱,每天枪炮各种乱乱糟糟的,你该做的事情你都要做。无论馆长还是什么部长、校长、下面的工友,该做的必须得做,虽然有各种困难,但这是职责所在。
我觉得人在任何时候都要做事情,再危难、再世道不济的时候,你还在做事,这是作为一个人在世界上你该尽的职责。我觉得这个很厉害。这些人身上都还有。
像组织抢运《赵城经藏》那个八路军太岳军区二分区政委史健,他是早期非常纯粹那种共产党员,有私塾的底子,十六七岁到北京读新式的学堂,参加过“一二九”。后来去延安,22岁直接去山西当县委书记兼八路军的政委。他不是一个简单的干部。那个时候“反扫荡”,朝不保夕的,他甚至把5000卷经藏分散,每个战士身上背几卷。
如果不是他们这么搞的话,谁知道那些东西会哪儿去了。要么被日本人抢走,要么可能就像很多国宝一样,慢慢因为各种原因,你偷一卷我抢一卷,没了,极有可能。但是现在非常完整,4000多卷在国图,全世界留存下来年代最久远的一套大经藏,这多厉害。像史健他就觉得自己该干这事。
尽管眼前的灾难看不到头
没有截止日期的乐观是最厉害的
北青报:而且好像人人还都有信心,就相信有一个未来。
杜兴:对。其实大家并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打赢日本,但就都觉得人在这个世上应该有信心。最典型的就是清华大学那个马文珍,他就是一个职员嘛。
北青报:嗯,他写的那些诗。
杜兴:他的学问应该不会太高,不像朱自清他们那种大学者。但是他那些诗,本身你说有什么,辞藻也不华丽,但是很有意思啊——“叮叮当叮叮当,陆游和杜甫又跟我们逃了一次荒”。
其实在他们内心,我想可能有更大的一个视野吧。中华民族一直多灾多难,我们说大一点,人类也一直多灾多难。尽管眼前的灾难看不到头,但他还是坚信我们一定可以的,一定能够战胜那些野蛮、不好的东西。这是一种无目的的乐观,没有截止日期的乐观是最厉害的,对吧?
其实你说这些事情,别看那么久远,它其实非常有当下性。我们经常讲世界危难,这个世界从来就不曾没有危难过,但是人你总还是有些你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些东西不能停下来。
北青报:挺棒的,我现在觉得得亏这个选题遇到的是你。
杜兴:没有没有,我也是受教育。你见识不同的人,肯定会给你带来很多感触,然后慢慢就会有一些东西出来。
我这两年慢慢发现,如果非要把我自己感兴趣的人和事做一个归纳的话,可能就是我刚才讲的,一种,在一个乱糟糟的世界里面,他有自己的一个秩序;第二种,他日常但是又有奇迹。这东西你叫它什么好呢?
反正一旦深入,我发现就会被这种东西触动,被它触动我才会有表达欲。采写/本报记者 吴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