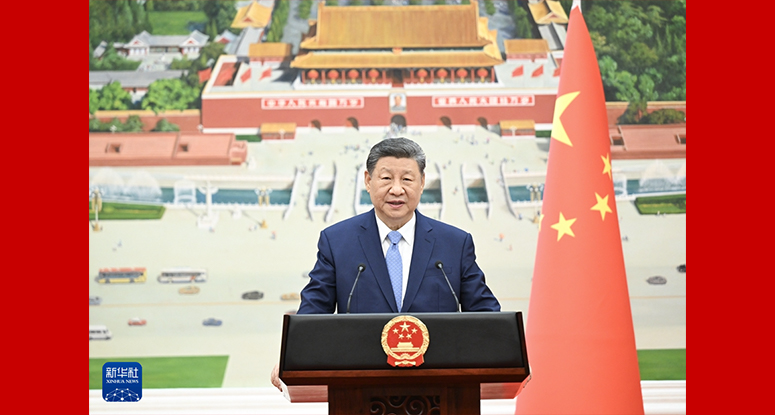探访抗战时期独一无二的延安日本工农学校
“1979年夏天,我们6人再次访问了延安,那是时隔34年的故地重游。对我来说,与其说是‘访问’,不如说是‘回老家’。延安是我的第二故乡,我青年时代在那里接触到了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如果不介绍出处,人们难以想象,这段饱含深情的讲述,出自一位昔日的侵华日军士兵之口。抗战期间,被八路军俘获的日本军人香川孝志,在延安接受教育改造,度过了令他终生难忘的时光。
宝塔山每天迎接着南来北往的游客。半山腰背后,游人罕至处有几排窑洞。窑洞中,深藏着一段历史。
8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曾在这里创办了一所人类战争史上独一无二的学校——日本工农学校。上千名深受军国主义思想毒害的日军战俘,于此接受教育、改过自新,有人再次返回前线时,已由战争分子转变为反法西斯战士。
“在这个学校里,真理战胜了邪恶,进步战胜了落后,文明战胜了野蛮,一切蒙蔽、欺骗被戳穿、被抛弃,和平、友好的理论在现实中生根、发芽……”担任过日本工农学校副校长的外交家赵安博,曾撰文这样回忆。
“我们对于日本无产阶级的士兵并无冲突”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挺进前线开展对日作战。随着战事推进,我军俘获的日本战俘越来越多。如何对待战俘并对其开展有效的教育感化,是我们党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
“1940年百团大战后,八路军俘获的日本军人陡然增多。除了部分释放或移交给国民党外,战俘大多分散在八路军各部。他们受军国主义思想毒害较深,反动顽固,需要有一个安定的改造环境,部分日俘也希望得到重新学习的机会。”延安革命纪念馆原副馆长霍静廉说。
事实上,宽待俘虏、将普通日本士兵同军国主义者区分开来,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思路。
早在1936年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时,毛泽东就指出,“我们对于日本无产阶级的士兵并无冲突,我们要用一切方法使他们站起来,反对他们本国的法西斯压迫者。”
1937年10月,在与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毛泽东再次明确,“瓦解敌军和优待俘虏”是八路军政治工作的三条基本原则之一。他说:“我们仍然把被俘的日本士兵和某些被迫作战的下级干部给以宽大待遇,不加侮辱,不施责骂,向他们说明两国人民利益的一致……将来抗日战场上如果出现‘国际纵队’,他们即可加入这个军队,手执武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在这一思路的指引下,日本工农学校应运而生。
1940年春,驻共产国际的日本共产党人冈野进抵达延安。经他提议,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政治部决定创办一所专门改造日军战俘的学校。
当时,关于学校的选址,曾经历了一场激烈的讨论。
“学校选址在宝塔山半山腰上的原‘东北地区干部学校’旧址内,有人提出反对,认为宝塔山是延安的标志,不宜为战俘居住。”宝塔山景区讲解员谢羽说,八路军总政治部斟酌再三,认为这里安静且空间较大,可以为学员提供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考虑到战俘大多出自日本平民家庭,毛泽东亲自将学校定名为“日本工农学校”。
然而,对这些深受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思想毒害的军人进行改造,又谈何容易!在押送战俘赶赴延安的路上,一场场考验就已经开始。
“绝食、谩骂、抵抗,甚至想杀害八路军战士,这些日本兵非常顽固。但在我们的真诚感化下,有些人的思想开始转变。在路上,八路军战士甚至会背着受伤的日本兵,这让他们很受感动。”霍静廉说。
在一部名为《幸运的人》的回忆著作中,曾任日军军医的佐藤猛夫谈及了他的逃跑计划——
被八路军俘获后,他经常在早晚散步时观察地形、伺机逃跑。直至有一次他突发高烧,失去知觉三天三夜,八路军医护人员给予他无微不至的照料,还给他带来稀有的酱菜。自此,他彻底被感动了,打消了逃跑的念头,又重新穿上白大褂,开始为伤病员治病。
1940年10月,晋西北等地首批日军战俘抵达延安,学校随即开始教学。中共中央从延安各界选派了一批精通日语的人员和较早转变思想的日本战俘担任教员。当时,学校的设施为一间约200平方米的教室,能容纳100多人就餐的食堂和6孔学员窑洞宿舍。冈野进曾回忆,“窑洞墙上涂着白粉,因此显得很明亮。”
顽固的日本战俘被感化
1941年5月15日,日本工农学校举行开学典礼。冈野进此时已化名为林哲,担任学校校长,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政治部敌工科科长赵安博担任副校长,学校校训为“和平、正义、友爱、勤劳、实践”。
次日的《解放日报》详细记录了这场典礼的盛况:15日下午6时,在八路军大礼堂,朱总司令、各界代表及学校全体学员参加了开学典礼。主席台上悬挂着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盟旗、日本工农学校校旗,以及毛主席为大会的题词“中国人民同日本人民是一致的,只有一个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
朱德总司令在讲话中说,希望不久的将来,日本工农学校学生能回国组织日本的“八路军”,来与中国的八路军携手,共同为争取中日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随后,学校全体学员登台宣誓。典礼上还表演了文艺节目,演出了日本歌曲、舞蹈和日语话剧《前哨》。“至夜十二时,大会在欢洽的空气中宣布结束”。
长期研究日本工农学校办学史的延安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常改香说,这场开学典礼,体现了中国人民和八路军对日本士兵的真诚关怀,热烈温馨的场面打动人心。学员小林清在第二天召开的座谈会上说:“一年多来支配我的全部思想的俘虏观念,直到昨天的大会上,才完全地消失了。我的思想解放了,我再生了!”
然而在此时,多数日本战俘还远没有这样的思想觉悟。
1942年6月12日的《解放日报》曾这样记载:“做了中国军队的俘虏,他们起初认为是莫大的耻辱。即令在学校多方面体贴、安慰下,他们仍是坐立不安,自暴自弃,十个中有九个企图逃跑或者跳崖自杀。在生活上早晨不起床,不洗脸,随地大小便等,来表示消极的抵抗。”赵安博也曾写道,学校宣告成立时,学员极为怀疑,以为八路军要“赤化”他们,利用他们反对日本。
对于这些思想极其顽固的日军战俘,学校制定了详细的教学计划,开设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还根据学员们的文化程度分为不同的学习小组。
开学第一年,课程主要有时事与日本问题、自然科学、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等。到了1942年,随着学员思想觉悟、理论水平提高,教学内容也由浅入深,增加了联共(布)党史、政治常识等课程。
“在政治理论教学中,学校特别注重学员对理论系统、深入的掌握。为此,1942年的‘时事与日本问题’课程安排了如共产党宣言、农业生产衰落及农村危机、资产阶级的壮大、工人为什么组织工会、日本法西斯的弱点之类的内容。”常改香说。
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让许多学员的世界观开始改变。
1942年下半年,一些学员开始学习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著作。学员前田光繁后来回忆道:世界观和人生观是很深刻的学问,之前我从未接触过。过去我认为日本有万世一系的天皇,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对于社会结构我根本不懂,对那些封建迷信的东西无从怀疑……经过反复学习,我觉得书中讲得有道理,开始积极参加有政工干部参加的讨论会。
日本工农学校还开设各种座谈会、讨论会,以启发式、互动式的教学改造战俘思想。当时,在学校最著名的“日军暴行座谈会”上,学员们揭露了日军轮奸妇女、活埋平民、用活人练刺刀、用瓦斯毒杀百姓的惨无人道的暴行。他们越讲越气愤,开始反思受到的毒害教育,逐渐认识到侵略者的邪恶本质。
与此同时,学校教员们朴实无华的生活作风、热忱细致的工作态度展示着马克思主义者的魅力,也在无声中感化着日本战俘。
香川孝志在他后来所著的《八路军中的日本兵》一书中回忆,中国教师王学文总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把深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解释清楚,重要的地方反复讲。他经常脚穿草鞋、头戴草帽来给我们上课。有一天下大雨,我们认为“王先生大概不会来了吧”。但他却卷着裤腿,渡过正在涨水的延河按时来讲课。“他的工作热情和严格要求自己的精神,使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
“我渐渐感到在无边的黑暗中,已摸索到一线曙光”
对这些曾犯下累累罪行的侵华日军战俘,中国共产党人没有打压报复,反而对之平等相待,为他们创造了良好的学习条件,生活待遇甚至远超八路军战士。即便是在陕甘宁边区遭遇国民党反动派封锁、陷入极大困难之时,边区政府仍把日本工农学校作为第一类供给单位,尽最大可能提供所需物品。
在日本工农学校旧址,一张菜谱记录了1943年学校的伙食状况:从周一到周六,每日餐食均有羊肉、猪肉或牛肉,主粮不是小米而是白面。牙刷、手巾、鞋子、肥皂等用品都供给充足。
当时,日本工农学校学员每人每月领取3元津贴,而八路军排级干部仅有2元。由于保障水平较高,有的学员在星期天还到街上去买两盅高粱酒喝。
宝塔山下、延河之滨,日军战俘得到了中国人民兄弟般的友爱。宝塔山景区讲解员秦莹说,日本工农学校没有高墙,没有荷枪的士兵看守,课后学员可以自由活动,同其他学校没有两样。
小林清曾在回忆文章中如此吐露心声:“学校和中国的同志们都十分尊重我们的人格和自尊心。在这一环境里学习、生活,使我们渐渐地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在异国他乡的日本士兵……无论在物质生活方面,还是精神生活方面,都完全是自由自在的,没有什么受束缚的感觉。”
除了提供优厚的生活待遇外,日本工农学校还创办了图书馆、俱乐部,经常举办舞会、演出等文艺活动,学员们跳樱花舞、编演反战话剧、高唱革命歌曲,课余生活十分丰富。有学员回忆道:“我们平时的文体生活有打麻将、扑克和下围棋、军棋,有时也打棒球。”
1941年5月8日的《新中华报》曾报道,“当时宝塔山下的延河河滩较宽,是一个很好的棒球场地。”有时,中央首长散步,偶尔赶上学员们打棒球,也饶有兴趣地观看。
延安现存的大量资料图片定格了日军战俘当年的生活场景。学校旧址内一张照片中,森健、秋山良照等8名教员和学员身着八路军军装,站在宝塔山下,他们个个面带微笑、目光炯炯,神情中写满了重获新生的快乐。
正义的力量、仁慈的感化,让这些受到军国主义蒙蔽的日本战俘的思想发生巨大转变。
学员大古正曾在1942年7月的《解放日报》上发表一篇名为《我的转变》的文章,他说:“到日本工农学校学习半年以后,我渐渐感到在无边的黑暗中,已摸索到一线曙光,那就是因为我们学习了共产主义及其他无产阶级解放的知识……我将和中国八路军一起,献身于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军国主义,为求得中日两民族的解放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优待感化战俘的举措,甚至连进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也大为震惊。
1944年10月,美军观察组约翰·埃默森等人到日本工农学校考察后,认为中共对日俘的教育改造是成功的。其撰写的报告中这样描述:一个日本工农学校的学生进入学校以后会感受到一种舒适友好的氛围,他们身边全都是日本人……
民主人士黄炎培在他的《延安归来》一书中也曾写道:“我感觉这一个日本工农学校,生气蓬勃得很。”
化敌为友的学校创造了奇迹
随着时光的推移,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日本战俘身上,发生了许多不可思议的变化。
常改香说,大生产运动开展后,按照政策,日本学员并无生产任务,但他们受到边区军民生产热潮的感染,主动要求参加劳动。他们成立了纺织组、农业组、木工组等,开荒种菜、自盖房屋、帮百姓锄草。1943年秋天,学员们收获了1万斤土豆,9石大豆,到1944年底,木工组已做出纺车103辆。
许多人或许难以相信,中国共产党宽大的战俘政策,甚至给予他们平等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
1941年10月,陕甘宁边区根据“三三制”原则举行第二届参议会选举,日本工农学校的森健当选为参议员。
在竞选中,他慷慨激昂地说:“我们这些生活在中国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日本人,有幸能够参加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选举,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给我们的一个学习新民主主义政治的好机会,这将为我们打倒反动封建的日本军阀政治、建立民主的新日本积累宝贵的革命经验。”演讲获得现场热烈的掌声。
随着改造的推进,一些日本工农学校学员积极参加八路军、新四军及日本在华反战组织,信仰战胜了血统,从战俘转变为反法西斯战士。毛泽东所预言的“国际纵队”成为现实。
谢羽说,学员们在前线发放传单、书写反战标语、制作慰问袋,到火线喊话,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战俘政策。他们同中国人民并肩作战,有的还献出了生命。
“晴朗的天空,阴暗的心,把无意义的战争停止。弟兄们,归国去吧!”学员们还创作出大量反战歌曲,到前线向日军传唱。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30日,在延安王家坪礼堂,八路军为即将回国的日本工农学校学员举行了隆重的欢送大会。9月18日,学员们离开延安。
至此,日本工农学校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它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在世界范围内绝无仅有的学校。从1940年筹办到1941年5月正式开学,再到1945年停办,加上山东分校、晋西北分校、华中分校等在内,先后有上千名战俘在日本工农学校接受教育。”常改香说,学校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的伟大创举和光辉实践,是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
尽管学校就此停办,但它所教育培养出的日本学员中,有的回国后撰写回忆录揭露日军侵华罪行,有的继续从事反战宣传,终身为推动中日友好而奋斗。
其中,香川孝志和前田光繁合著的《八路军中的日本兵》描述了他们从“皇军”成为反战斗士的经历,介绍了八路军英勇抗战的事迹,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佐藤猛夫写成《幸运的人》一书,为防止军国主义复活、主张中日友好奔走呼号。改革开放后,香川孝志、前田光繁等多次重访延安,为增进中日友好做出了贡献。
在这些学员中,小林清是唯一没有回国者。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天津市社会科学院工作,曾任天津市政协委员,晚年还加入了中国国籍,亲眼见证了新中国的建设成就。1985年,他完成了回忆录《在中国的土地上——一个“日本八路”的自述》,留下宝贵的一手材料。1994年,小林清在天津与世长辞,他的骨灰一半被带回日本、一半埋在天津。
2015年8月15日,小林清之子、日本八路军新四军战友会事务局局长小林阳吉在《人民日报》撰文,深情回忆了父亲与中国人民并肩作战的日子。
文章中写道:“父亲曾说,我爱日本,因为那是我的祖国,我生长的地方,那里有我的亲人和许多值得怀念的人们。但是我更爱中国,爱那些在艰苦战争岁月和坎坷生活中和我同生死、共患难的中国人民。”(记者陈晨、李华、吴鸿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