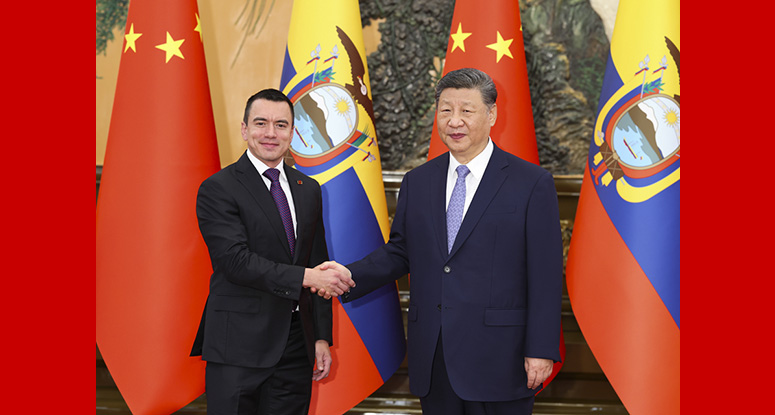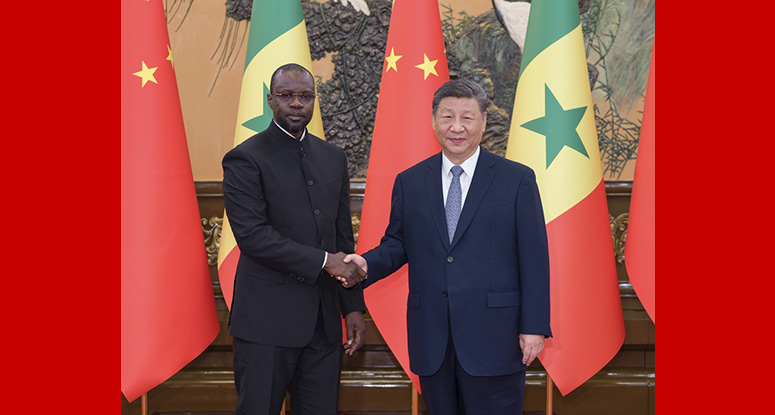传承老北京非遗的年轻人
传承老北京非遗的年轻人(青春派·青春奋进新时代(34))
3000多年建城史、860多年建都史——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北京拥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126个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273个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如何传承好这笔宝贵财富,为人们的美好生活赋能?一群喜爱非遗的年轻人不断探索,蹚出了一条条新路。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京绣代表性传承人田鹏:
“京绣不仅要活在过去、现在,也要活在未来”
田鹏是京绣第五代传人。
京绣又称宫绣,作为“燕京八绝”之一,起源于唐代,明清时期开始兴盛,多用于宫廷装饰、服饰。田鹏说,他的祖太姥爷梁枝在清朝皇宫的绣花局当绣工,京绣非常精细,一个巴掌大的花朵也需要绣上万针。
在田鹏印象中,因为长年绣花,姥爷拿绣花针和顶针的手指上结了厚厚的茧子,两个肩膀也不一样高低。年幼的田鹏时常帮母亲梁淑平劈线、穿针,看着绣花针在闪着光的绸缎里外上下翻飞,缎面上精美的图案让他啧啧称奇,不时在母亲指导下饶有兴味地绣上几针。
“大小伙子干吗当绣娘?”2008年,田鹏大学毕业,面对外人的不解,他内心开始动摇,到北京首都机场当上了安检员。
“这门手艺不能断在我们手里,要好好传下去!”经不住母亲再三劝说,也割舍不下对京绣的喜爱,工作两年后,田鹏辞职,投身京绣事业。
京绣看上去很简单,4块木板将绸缎夹紧,再有一根绣花针就够了,但一上手就知道并非易事。“京绣常用的针比头发丝略粗,一般人拿都拿不住,更别说干活了。每一针的要求也非常高,稍一疏忽整幅作品就毁了。”田鹏深有体会,完成一件绣品需要打板、打草图、画图、扎眼等十来道工序,每道工序都不能有一丝马虎。
齐针绣、抡针绣、平金绣、打籽绣、垫绣……在母亲的悉心指导下,田鹏技艺渐长,熟练掌握了十几种针法,对色彩的搭配也得心应手。他还到北京联合大学参加京绣培训班,到北京服装学院、江南大学等地学习服装设计、裁剪。
京绣技艺虽难,开拓市场更难。因为工艺繁复、用料考究,京绣的成本很高,价格昂贵。由于社会需求有限,京绣市场不断萎缩,技术濒临失传。梁淑平的绣厂最多时有2000多名绣娘,慢慢只剩下几百人,年轻人屈指可数。
“京绣不仅要活在过去、现在,也要活在未来”,田鹏首先在京绣图案上下功夫。传统京绣图案讲究“图必有意,意必吉祥”,常用谐音、会意、借代等方法,表达祈福纳祥的美好意愿,传统图案大多为花鸟、人物。田鹏大胆创新,增添了现代元素。
有一位客户,希望定制一份礼品送给俄罗斯朋友。田鹏将俄罗斯风景和六角雪花、冰凌等图案融合在一起,制作了一幅冰川雪景图,客户喜出望外。他还将传统百子图与滑雪、滑冰、冰球等图案相结合,开发出冬奥系列产品,让人耳目一新。
除了传统门店,田鹏还开设了网店,在短视频平台直播带货,拓展销售渠道。他尝试跨界经营,京绣元素被运用于汽车内饰、网络游戏之中。
“这孩子有想法!”京绣的销路逐渐被打开,梁淑平喜不自禁。2013年,田鹏注册了“淑平京绣”商标,现有传统服装、现代服装、家居用品、装饰画、伴手礼5个系列数千种产品。销路好了,绣娘们的收入也逐年提高,如今每月平均收入3000元左右,一些建档立卡贫困户因此脱贫。
“原来这就是京绣,太美了!”京绣是一门小众的非遗项目,过去许多人难得一见,见到的人都赞叹不已。
“一定要让更多人了解京绣、爱上京绣!”田鹏暗下决心。这些年来,他带着京绣走进了学校、社区、公园和商场,一边展示一边传授技法。更让田鹏期待的是,集收藏、展示、培训等功能于一体的京绣文化产业园年内将落户河北省定兴县,这名85后把一门老手艺干成了大产业。
京韵大鼓代表性传承人李想:
“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传统艺术才能赢得更多观众喜爱”
周日下午,北京老舍茶馆小剧场里,观众们听得入神。只见李想身着紫缎绣花旗袍,款款走上台来。一曲《伯牙摔琴》唱罢,台下掌声阵阵。
“这姑娘演出很投入,这些年进步很快,今儿这一出听得真过瘾!”88岁的老戏迷刘焕荣连声夸赞。
今年36岁的李想,学习京韵大鼓已有26个年头。
李想自幼喜欢唱歌跳舞,电视上的相声、小品节目也让她入迷。小学四年级时,她就读的天津市宝龙巷小学组建少儿曲艺团,听到学校大喇叭里播放的招生通知,李想赶紧报了名。
李想起初学习小品,因为曲艺团没有经费置办道具,她迟迟没有演出机会。曲艺团的负责老师杨长惠看在眼里,特意在一次演出中安排她当主持人。
“你想学京韵大鼓吗?”见李想主持时毫不怯场,嗓音条件也不错,杨老师问她。
李想与京韵大鼓的缘分就这样开始了,那一年,她10岁。
平日里跟着磁带反复学唱、练习打鼓板,每周二下午与乐队合乐……李想对京韵大鼓的喜爱与日俱增。1996年1月,曲艺团在天津黄河道影剧院举行专场演出。李想最后一个登场,把《丑末寅初》《重整河山待后生》两首经典作品唱得有板有眼,颇有骆派京韵大鼓的味道。
“小学生把京韵大鼓唱得这么好,太难得了!”看到媒体上的相关报道,著名京韵大鼓表演艺术家骆玉笙喜出望外,辗转与曲艺团取得了联系。
大约一周之后,求才心切的骆玉笙特意来到学校。听李想带领100名学生唱完《重整河山待后生》,82岁的老艺术家欣喜不已,当下收她为徒。
“骆派京韵大鼓的声音不能断,要好好传下去!”骆玉笙语重心长。京韵大鼓是在清末由河北沧州、河间一带流行的木板大鼓发展而来,骆玉笙博采众长,形成了刚柔并济、以声传情的艺术风格。她的音区跨越3个八度,有着“金嗓歌王”的美誉。老人把数十年的从艺经验倾囊相授,一字一句悉心指导,帮助李想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
名师指点,加上数十年勤学苦练,李想的技艺日臻成熟,成为骆派京韵大鼓的代表性传承人。
“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传统艺术才能赢得更多观众喜爱。”李想说。她大胆尝试古曲新唱,《丑末寅初》通常由三弦、琵琶和四胡伴奏,改用电吉他、贝斯、钢琴伴奏,音乐性更加丰富,让人耳目一新。在鼓曲情景剧《尚·韵》中,她借鉴话剧元素,将击鼓表演与演唱完美结合,一曲《击鼓骂曹》生动传神,一举夺得中国曲艺最高奖——牡丹奖的新人奖。
2005年,李想进入北京曲艺团工作。除了演好每一场戏,培养新人、推广京韵大鼓是她最大的心愿。
刚跟李想学艺时,柯琳是北京科技大学的大一学生,李想并没有因为柯琳是业余爱好者而放松标准,为她制定了周密的学习计划。经过多年习练,柯琳技艺渐长,曾在北京市群众曲艺大赛等多项比赛中获奖,此后成为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史论专业的研究生。
相较于师承制,“非遗进校园”给了更多孩子亲近传统技艺的机会。今年以来,每周三下午,李想都要去北京小学万年花城分校上课。几节课过后,这些零基础的学生无论吐字发音还是旋律节奏都进步不小。对此,李想倍感欣慰:“只有让孩子们接触到京韵大鼓,才有可能喜欢它,甚至愿意投身其中。”
核雕、雕漆代表性传承人马宁:
“雕漆不应是高高在上的艺术品,应该走入千家万户”
略胖的体形、身穿灰色中式上衣……“80后”马宁看上去很老成。
他从事的行当更古老。核雕和雕漆均有1000多年历史,马宁是这两个非遗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
核雕是马宁的家传手艺,太爷爷马仁寿在清朝光绪年间便以小件雕刻而闻名。在马宁的记忆里,小时候家中灯绳上拴的,都是爷爷马荣春雕刻的各式各样核雕,煞是好看。
年少的马宁,对美术有着浓厚的兴趣。因为就读的学校与琉璃厂相距不远,一有空,马宁就去那儿转悠。14岁那年,马宁主动要求爷爷教他核雕。
核桃坚硬,一不小心刻刀就会扎破手,起初马宁手上净是伤痕。长时间顶着刻刀,他右手中指指甲都挤歪了。
“一天不拿刻刀就难受!”初三时,马宁右手骨折,他就试着用左手雕刻,这竟让他成了为数不多的能左右手雕刻的工匠。
良好的美术基础,加上勤学苦练,马宁很快就成了核雕能手。核雕多以核桃、桃核为材料,就其自有的纹理雕刻而成。渐渐地,马宁感觉到核雕受材质的限制太多,无法做出震撼人心的作品。
2010年的一天,一位朋友告诉马宁,有几位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面向社会招收传承人。马宁赶紧报了名,并选择了雕漆这一项目,“雕漆空间大,可以让我的艺术想象力得到充分发挥。”
雕漆工艺复杂,周期很长,一件雕漆作品一般要制作一年甚至更长时间。其中最耗费时间的是“髹漆(将漆涂在器物上)”,雕漆通常需要16毫米厚的漆,必须髹漆300道左右。髹漆的最佳温度为23摄氏度到30摄氏度,湿度80%,工匠在阴暗闷热又潮湿的车间工作,大汗淋漓。
“因为我喜欢这个行当,所以愿意吃这份苦!”凭借着扎实的雕刻技艺功底和对艺术的独特理解,仅学习两年,马宁就能独立完成雕漆作品的制作。2014年,马宁和朋友兴冲冲开了一家店铺,一股脑儿进了许多雕漆材料,准备大干一场。
不料,雕漆成本高、价格贵,许多顾客光看不买,生意很冷清。不到半年,马宁就赔光了老本,一起开店的朋友走了,店铺无奈关张。
马宁没有气馁。在居委会帮助下,他在小区地下自行车库里圈了一个小角落当工作室。地下室很潮湿。马宁全然不顾,整天在台灯下埋头创作,饿了就用馒头抹酱豆腐充饥。
一年半后,一座高2米、宽1米、重86公斤的水月观音佛像完工,作品有多处创新。马宁巧妙结合木雕、象牙雕刻的手法,使人物无论从正面还是侧面看都栩栩如生。这件作品先后获得多项奖项。
“雕漆不应是高高在上的艺术品,应该走入千家万户。”随着经验的不断积累,马宁开始尝试将艺术与生活相结合进行创作。他改变了以往将漆全部包裹在茶壶上的做法,而是保持壶把、壶嘴原样,只在壶身部位进行雕漆制作。这样不仅保持了茶壶本身的功能,同时发挥了雕漆的装饰和隔热作用,使雕漆茶壶成为一个实用的艺术品。
湖北省十堰市竹溪县是重要的生漆原产地,曾是国家级贫困县。2016年,马宁出任竹溪生漆产业发展高级顾问。经过他和众多专家的努力,当地将一座老漆厂改造,建成了一座生漆博物馆。目前,竹溪县共有漆林10多万亩,生漆产业成为当地支柱产业之一。马宁不时去现场指导,还通过工人拍摄的视频,实时了解漆艺扶贫车间的生产过程,及时帮助工人解决技术难题。凭借着雕漆手艺,竹溪县昔日的贫困户如今一天能挣七八十块钱。
(吴健坤参与采写)
本报记者 施 芳